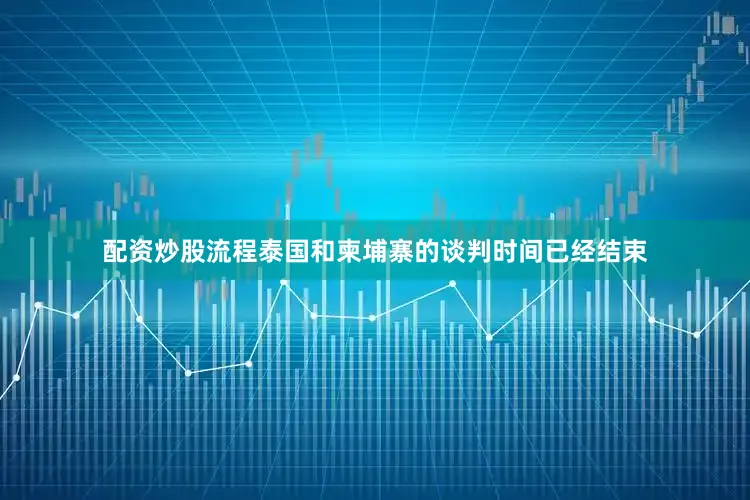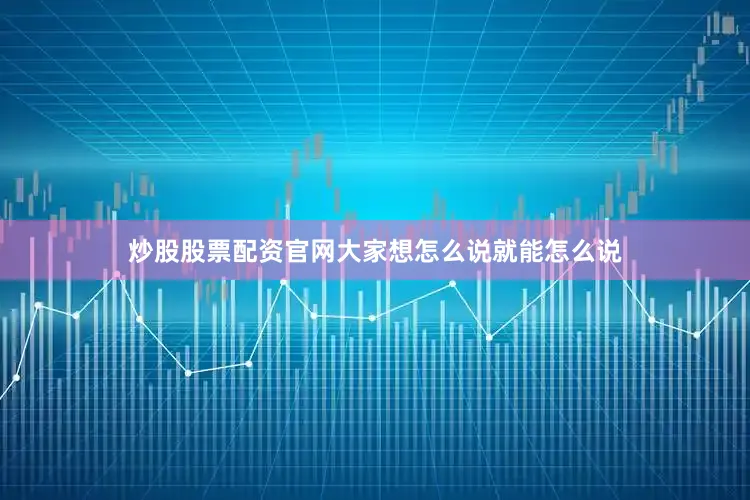
李荣建教授大概没有想到,因为杨景媛事件,他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现在被挖出来批判了。一个不知名的教授,一夜之间,成了全网讨论的“名人”。
这篇论文名为《与商汤关系新论》发表在《武汉科技学院学报》之上。那个时候,大家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也没有“为了文化的自信”的说法,所以也显得更具代表性。

在这篇大作中,李荣建教授认为,《汉谟拉比法典》实为中国商朝开国者商汤所作,汉谟拉比与商汤实为同一人
汉谟拉比约生于公元前1810年,卒于公元前1750年。商汤约生于公元前16701587年。二者之间,相差一百多年。于是,李教授认为,二者在时间上的差距可因远古历史推算误差而忽略
同时,李教授还宣城,翻译传播《汉谟拉比法典》的英语,实际上源自于汉语,是对汉语标音后的产物
至于其目的,很简单,一切为了服务“中国起源说”。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第一个问题:商汤时代有没有文字?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出现于殷商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前1046按公元前年算,此时商汤已经死了差不多300年。
在商汤时代,甲骨文还不存在,至少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没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体系。注意,我说的是文字体系,不是文字符号。
在上朝早期的遗址中,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确实发现了少量刻画在陶器等器具上的符号,但是,这些符号是否属于文字尚无定论。
那么,既然商汤时代还没有文字体系,又何来商汤制作《汉谟拉比法典》一说呢?
反观《汉谟拉比法典》所用的楔形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到《汉谟拉比法典》出现时,这种文字已经使用了接近年,相当于我们今天到三国时期、西周初年到唐宋时期的跨度。
一套使用了近年的文字体系,足够形成完整的语法规则与书写规则,精准记录法律条文、商业契约等复杂内容
所以,认为是商汤制作了《汉谟拉比法典》,与山顶洞人写出了《论语》一样的荒谬。

第二个问题:甲骨文与楔形文字能否互相转化?
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而楔形文字是表意兼表音的音节文字是分属不同文明、毫无亲缘关系的两种文字体系
楔形文字诞生于两河流域以芦苇杆等为书写工具,写在湿泥板上。待泥板干燥之后,再烧纸硬化。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泥板能保存那么长的时间,秘诀就在烧纸。如果你还不能理解,可以去博物馆看看陶瓷与砖块,很多历经几千年都保存完好。
甲骨文诞生于黄河流域,刻于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服务于占卜祭祀,始终以象形表意为核心,未发展出表音体系。汉字要到清朝末年,才形成表音体系,这就是以前的注音符号和后来的拼音。至于东汉时期就出现的切音,是用两个汉字切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前字取声母,后字取韵母和声调。比如,“河”字在《说文解字》注为“胡歌切”,“冬”在《广韵》中标注为“都宗切”,但本质上依然不具备表音功能。
楔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跟现在的英语差不多。而甲骨文一个符号多对应一个事物或概念“日”写作圆形中间加一横楔形文字与甲骨文的符号系统、书写逻辑、表达规则完全独立不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

第三个问题:《汉谟拉比法典》是什么?
出土于1901年的伊朗苏萨遗址,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收藏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刻在高2.25米的玄武岩圆柱上。圆柱顶部刻有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象征“君权神授”。下部可有282条法律条文,涵盖民事、刑事、商业、家庭等领域
与同时期同地域的出土物也不少。
比如,汉谟拉比书信泥板,由法国考古队在叙利亚马里城邦遗址发掘,一共有2.5万块之多,记录了汉谟拉比对关于的指示,对司法的判决,可以与法典相互印证。
比如,现藏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普林顿322号泥板,刻有土地测量与税收计算之法,与法典中“以几何划分土地”的实践高度相关。
再比如,伊拉克尼普尔遗址出土,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尼普尔恩利尔神庙泥板,记录了神庙粮食分配、祭司薪酬等经济活动,与法典中“若祭司挪用神庙财产,需赔偿30倍”的条文直接关联。
上述文物均出土于伊拉克中部的巴比伦、尼普尔、乌鲁克等古巴比伦核心城市,或邻近的叙利亚马里城邦,经对文物本身,或者与这些文物同时埋葬的其他物品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均集中在公元前1800-前1600年,与法典年代高度吻合。
很多人认为,《汉谟拉比法典》是一件孤品,没有证明能力。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同时期的许多文物,都能证明《汉谟拉比法典》是一件真品,并不存在孤证不立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李荣建教授的“研究”为何站不住脚?
作为武汉大学的学者,李荣建教授发表此类观点,更值得警惕。
我特意查了一下李建荣的百科资料。
出生于1955年的李建荣教授今年已经整整70岁,发表作品时,他5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以下是李建荣教授的简历。
1977年8月,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工作任武汉大学外语系教师
10—19809月,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干部
19844武汉大学历史系助教
51987中建总公司驻利比亚经理部A组翻译
19871988月,回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助教
61991武汉大学历史系讲师
1992月,成为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1996月,继续担任
1997月,升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8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文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200012月,回国担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112003月,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一等秘书、政治处副主任
月继续担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4约,成为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
2006年,升任教授

从李建荣教授的简历来看,有几个问题。
第一,他并没有历史学背景,大学专业是阿拉伯语。
第二,他没有研究生学历,更没有博士生学历。
第三,一个学阿拉伯语的人,干的却是教历史的活,是否合理?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阿拉伯文化与国际关系,并非考古学、古文字学或亚述学,对《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时代的历史背景缺乏专业积累。而且,就算他懂历史,懂的也是阿拉伯的那一部分,对中国史,他真的很熟悉吗?从他的论文来看,他对甲骨文一窍不通。
在他的论文《<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中,既未引用任何楔形文字原始文献,也未参考甲骨文研究的权威成果,仅通过对个别词汇的牵强附会(如将“汉谟拉比”发音与汉语某词强行关联)便得出结论。这种“研究”完全违背学术规范!
历史学结论需以考古证据、文献互证为基础,而非主观臆断的“文字游戏”。
而玩这类谐音梗游戏的人,真的不要太多!有一个所谓的西方伪史论者,将谐音梗玩出了新高度,连伪史论大师黄河清都看不下去了。
说到黄河清,我还要多说几句。

从本质上来说,李建荣和黄河清是一类人。
李荣建在《与商汤关系新论》中提出的观点严重违背历史学界的普遍认知和研究成果黄河清的伪史论观点也是如此,缺乏严谨的论证和证据支撑。
不是说不能质疑西方的历史,只要有证据,谁都可以质疑。而李荣建与黄河清得出的结论,完全不是通过严谨的论证得出的,而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必然是这样。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不是学考古的,甚至也不是正儿八经学历史的。这类所谓的教授,平时忽悠一下本科生还可以,忽悠一下无知网民还可以,站在真正的专家群体中,他们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质疑西方历史,这是合理合法的。但编造谎言,穿凿附会,只为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比别人强,或者其他文明都是不存在的,中华文明才是唯一,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言论的本质,是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否定是对网民智商的捉弄,是对严肃历史的戏谑与侮辱。
俊升配资,炒股开户平台,配资114平台查询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